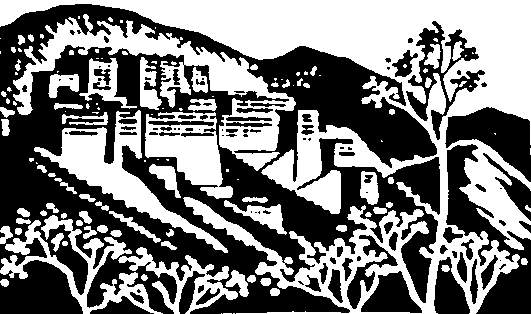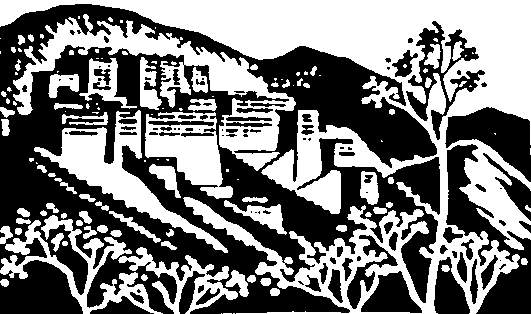花 魂
渭城朝雨 輕塵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
輕塵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
勸君更進一杯酒,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唐朝的王維所寫的這首詠別詩,後人千言萬語不能出其意之外,別離之際,細雨紛飛,一個“無”字,把場面襯托得多麽悲壯,歷代文人寫雨,總是愛寫小雨,又或是雨後天霽的景色,鮮有寫大雨的。印象中只有東坡的“雨已傾盆落,詩仍翻水成”是寫大雨的。大抵如無東坡的胸懷,很難駕馭大雨這類氣勢的意象。近人經營這類意象的成功例子,有毛主席的“大雨落幽燕,白浪滔天。”文人都不愛寫大雨,或許是都嘗過在大雨下無傘疾奔的味兒,那種急急如喪家之犬,惶惶如漏網之魚的感覺,就是有什麽詩意,也給三步並作兩步的趕掉了。偏生在東南亞地區如澳門者,碰上雨季,這種愴惶奔逃的情況卻是屢見不鮮。這陣子的大雨一下起來,真是海龍王也管它不了。只管嘩啦嘩啦的下個不停,幾乎把澳門浸成澤國。低窪地區水浸了幾十年還是在浸,我們的年紀都是雙腿浸在污水裏邁過來的,只是年紀長了,不再愛雙腿浸在水中那種不乾不淨的感覺,於是盡挑些地勢高些的路來走。
湊巧這朝的雨勢不像渭城的那般溫柔得楊柳也在婆娑,只見急雨墮地,還碎起水珠萬千,趕路的人如我者,在這六月的暑天裏,竟被暴雨孤立在傘下發抖,交著雙臂於胸前,仍感到風雨像要鑽進皮膚裏似的,而腳下踏著的是一道落花堆成的路。
這邊的街道兩旁儘是些花園別墅,圍牆內的花樹總是要出牆而來似的,特別是這花放的季節,花兒怒發得像要把牆壓得塌下來般;然而這朝,燦爛的生命之火已被大雨淋熄,一朵朵花魂只作了別人腳下之泥,連落英那一刻的淒美也享受不了。
誰伴花魂度黃泉?恐怕也是西出陽關無故人了!